在虚实与城乡之间贴地飞翔
作者:《贵阳日报》记者 郑文丰 时间:2019-03-20 阅读:355
威宁籍作家宫敏捷推出小说集《锅圈岩》——
在虚实与城乡之间贴地飞翔
《贵阳日报》记者 郑文丰

宫敏捷
作家名片
宫敏捷,威宁人,现居深圳。青年小说家,评论家。有中短篇小说发表于《上海文学》《黄河文学》《湖南文学》《广州文艺》《特区文学》《南方文学》及《文学与人生》等刊物。出版小说集《锅圈岩》、评论集《写作,找到表达自己的方式》。
1997年,二十一岁的宫敏捷离开家乡威宁县二塘河谷,前往方言俗称为“田野间的深沟”的地方。这个地方叫深圳,那里的许多小地名都以“坑”或“田”命名,“乡土”得像在老家一样。2015年,在深圳结婚生子、安家落户的宫敏捷,第一次回家乡威宁探亲。他去了锅圈岩——藏于乌蒙群山深处的一个天坑,他的母亲就出生在锅圈岩附近的一个村子,他的小舅母依旧生活在这里。
见到小舅母,宫敏捷吃惊不已,“她就像她们家后山上的石头,几十年过去,模样都没有什么变化。”更让他吃惊的是,故乡外表变得现代了,但许多人的精神面貌和思想境界,就如小舅母的面貌,还停留在过去的日子里,人们像是被时间尘封在某一个点了。而他生活了二十多年的深圳,虽然地名依旧土气,但早已在日日新的“流动”中,进化为“开放”的代名词。
出生之地与生活之地,在“封闭”和“开放”的两端,形成了极具张力的文学场。宫敏捷隔着二十多年的烟尘来回张望,想到用文字重新塑造文学的故乡。2018年底,宫敏捷带着一部名叫《锅圈岩》的小说集与家乡读者见面,第一次以文学的方式返回故乡,并在贵阳钟书阁书店,与以文学的方式坚守乡土的作家冉正万对谈。
《锅圈岩》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是该社推出的“中国当代原创文学”系列之一。新书的书封是一幅色块地图,罗列有小说中涉及到的几处地名:母亲出生的“四梨村”,村名由少数民族地名音译而来;二表嫂的娘家“四区”,则带有民国年间划区而治的痕迹;作者本人出生和生长的“二塘河”,则一次次地在小说里游泳的儿童、过河读书的少年、回忆往事的中年人血液里奔腾着;沿着二塘河延伸的成昆铁路支线,以及错落分布的工厂……这些不同历史阶段的地名,如同时光沉积的一个个切片,以一种奇特得近乎魔幻的方式并存着。
正如冉正万老师所言,连绵起伏的封闭山头,比起一马平川的平原来,更适合写成小说。在宫敏捷看来,居住其间的各族山民,在日常生活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表达方式以及神话传说,“基于这些时代场景,我们真的可以写出比拉美作家更魔幻的东西来。”
在充满文学感的虚实、城乡间,宫敏捷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在他看来,不管怎么说,文学创作,就是在现实的基础上虚构另一个现实出来,前者贴地,后者飞翔。

浙江诸暨签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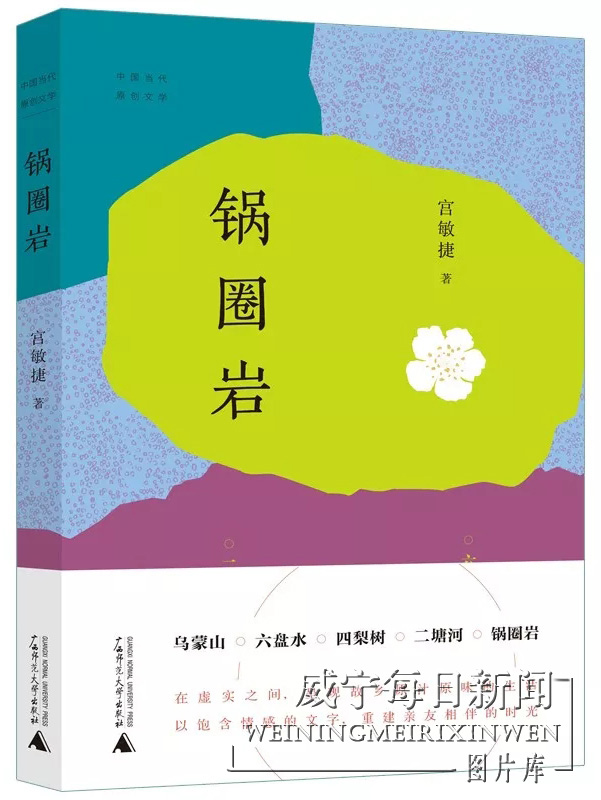
宫敏捷小说集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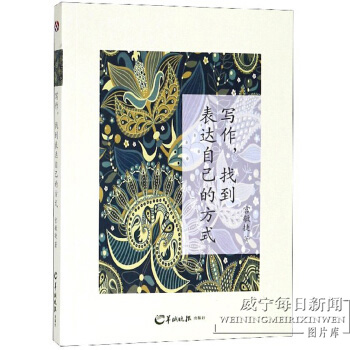
宫敏捷评论集封面

贵阳签售现场

浙江诸暨签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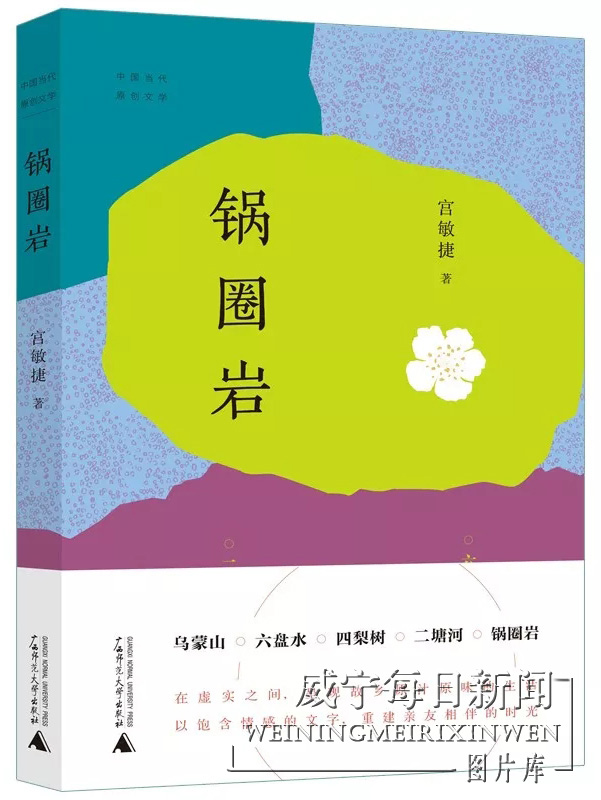
宫敏捷小说集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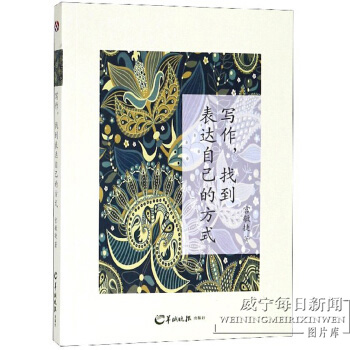
宫敏捷评论集封面

贵阳签售现场
山地比平原更适合写成小说
记者:有个说法认为,贵州的文化和地理环境是最接近拉美的。去年在贵阳举行的第五次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上,来自拉美国家的翻译家提到了一个观点,即认为拉美具有“混血性”特质:“我们用西班牙语,但同时也保留着印第安人的传统,我们的习俗、音乐、观念等还受到了非洲人影响。”你觉得“多彩”的贵州,和“混血”的拉美接近么?
宫敏捷:我对拉美的了解,都来自于拉美作家的作品。外界对这些作家的作品,最强烈也最统一的共识,就是魔幻现实主义。但拉美作家的代表人物加西亚·马尔克斯对此却是嗤之以鼻的,他说,现代文明像一把斧头一样砍进拉丁美洲的。他自评自己所书写的其实是拉丁美洲的现实生活,是他们的日常,而不是什么魔幻的东西。
读过《百年孤独》的人都知道,拉丁美洲气候炎热,许多人包括马尔克斯在内,连冰块都没有见到过,冰块就成了一个神奇的东西;他们也没见过磁铁,当吉普赛人拿着磁铁从村子里走过,许多消失多日的铁器物件,纷纷从草丛里,或者不知什么角落里飞出来时,他们自然对吉普赛人奉为神明了。
之所以造成这样的局面,就是因为拉丁美洲之于欧美的发展滞后,当欧美在发射卫星、建造航天飞机、把人送上太空、满街都是汽车到处乱跑时,拉美的许多人连冰箱是什么都不知道,甚至连凸透镜都没见过。这种经济发展不平衡带来的文化差异、观念差异,经拉美作家的神奇还原,对其他地域的作家,尤其是读者来说,就成了一种叫魔幻现实主义的东西了。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过去,西南山区由于交通不便,很长时间保持封闭状态,形成了多彩的“文化千岛”现象。生活其间的山民,他们的日常生活,与其他开放地区相较而言是互不可知的,作家只要思想性、文学性、艺术性地呈现出来,就是真正的魔幻的文学作品。
记者:乌蒙大山地域的独特性,是否也养育了具有独特性的山民性格?
宫敏捷:对外人来说,乌蒙大山是如此的浩渺与厚重,巍峨与雄壮;但对我们来说,它曾经又是如此的不可跨越。许多人会用诗歌的语言去描写它,说“山那边是什么/还是山”,落实到生活这个层面去考虑,你才会感觉得到,有时候,它带给我们的,除了交通的闭塞、经济的落后、环境的恶劣等等之外,还有前途不可预知的绝望。生活在这种地域的人们,除了种地,似乎没有什么选择,没有多少出路,所以许多人都有着双重的鲜明性格:山里人的淳朴善良以及对个人利益的过分看重;带着阴柔、阴沉与隐忍,就像家家户户门前大山上,始终萦绕着的薄雾,神秘而又美丽,但让人看不透。我是他们中的一员,出走了二十多年,回过头去,我也看不透。不过,现在一切都在变好,随着经济的发展,还会越来越好!
记者:能否这样理解,生活在乌蒙大山里的山民,天然就具有文学性?为什么?
宫敏捷:所谓“文学性”,其实就来自于地理、历史等原因造成的地方“封闭性”。由于封闭,就自成一体,由于走不出去,大家就自己建造自己的世界。这个世界的正常运转,更多时候靠的是村规民约、世俗伦理等等。
对于外面的人们,这似乎是另一个世界了,具有天然的神秘感,又具有天然的陌生感,这两个因素都会带给人们强烈的好奇心,想一探究竟。这个时候,小说家就有事可做了。
威廉·福克纳说他更多的时候,是让他笔下的人物,凭着“本能”行事。真的完全是本能吗?也不一定;只是他所塑造的人们,都有自己有别于人的是非观念和行为准则,我们是不能用自己的价值判断体系去衡量他们的。这给了我很多的启示,即如何将小说人物还原成他们最真实的自己,而不是把他们写成我想要的样子。如果不是如此,山民就与“封闭”环境之外的人们一模一样了,意义也就不存在了。
在虚实之间贴地飞翔
记者:在文学文体中,虚构文学地位崇高。我们知道,在世界范围内,虚构文学的地位位于文学的顶端,诺贝尔文学奖往往只评虚构文学,看不上纪实文学。结果前两年获奖的阿里克斯耶韦奇是个少见的例外,后来又颁给摇滚歌手鲍勃·迪伦。对此,北大中文系教授陈晓明先生有个论断:虚构文学本身呈现某种枯竭。意思是说,从莎士比亚到托尔斯泰,虚构文学经典迭出,但也很难花样翻新,作家的想象力已经日趋穷尽,虚构文学开始了世界性的衰退,诺贝尔文学奖实在找不到人了,只好找一个歌手垫一垫。你认为虚构文学面临困境了么?
宫敏捷:我是这么想的,诺贝尔文学奖不管是评给阿里克斯耶韦奇,还是鲍勃·迪伦,唯一的判定标准,一定是他们作品独特的文学性、思想性与艺术性,而不是虚构或者非虚构的问题。我也不认为,虚构文学会存在什么困境,文学自有其高度与深度,存在困境的是作家本身。当然,许多题材被无数前辈作家写到极致的现象确实存在,如《红楼梦》《战争与和平》《喧哗与骚动》《尤利西斯》《变形记》《老人与海》等等,我们无法翻新,也真的不可超越。但之所以说是作家本身存在问题,而不是虚构文学的问题,是因为一些作家不缺才情,也不缺努力,缺少的是一颗学习的心,以及沉稳又扎实的写作态度,当下急于表达,胡乱表达,甚至是一再重复自己的表达多了些。
当然,我们不能关起门来谈论这个问题。在全世界范围内来看,确实存在着虚构文学式微的问题,这不过是当下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渠道更多元了的缘故。加之现在要想成为作家,似乎越来越容易了,以致出现了作家比读者还要多的局面,所有读者都盯着那么几个作家作品看的年代一去不复返了,作家失去了明星光环,偶像光环,还有多少社会大众在关注作家,又写了什么东西呢?写得好与不好另说,是根本就不会用心去看了。
记者:虚构与真实之间很微妙。作家肖江虹说他每次写小说时一开始用的名字都是“我舅、我叔、我姑妈这些,写完了才找另外的名字把这些名字给替掉。”他说,拿亲人的名字来作为小说的人名,写起来特别容易投入感情,但要是用一个陌生的名字的话,得在写作过程中花费漫长的时间重新和这名字建立感情。你是如何与小说里的人物建立感情的?
宫敏捷:我也面临这个问题,我也这样做过。但是我现在找到了另外一个办法,就是在一篇完全虚构的故事里,安插一两个次要的却又是身边真实存在的人物,一般是那些我知道他们不可能看到我小说的人物,且不带有批判性质地书写,这样便于我带着激情又冷静客观地去书写虚构的人物。因此,在《锅圈岩》这本小说集,我多次提到我的小舅母,还写到了我小姨妈等。我觉得她们就存在于现实与虚构之间,作家与人物之间,是通过她们,把我们彼此连接在了一起;抑或说,有她们的真实存在,一切虚构的事物、人物,才有了一个可以依附的点,并在我的文字中,自行聚合力量。
有了第一篇小说作为基础,我再在这个小说里,生发出第二篇人物完全是虚构的作品来。我对我虚构成功的人物,是有感情的,他们身边同样是虚构的一些人物,又会引起我的注意,为其写一篇小说。这是我的一种创作方式,另一个方式是,我的一些小说,不是先有人物,而是有一个我感兴趣的场景,我是围绕着一个场景去设置人物,《锅圈岩》便是。这一类的小说,是文本成功了,我才慢慢对人物变得越来越有感情。这也是我喜欢回头去看自己小说的原因。
记者:你过去的小说多为都市题材。现在回头写故乡,内在的逻辑是否是因为你面临着一种“虚构文学的困境”——毕竟城市总被称为“无根”“流动”的存在,都市虚构文学不过是“无根飞翔”,故而这次“由虚入实”——即你所谓的“贴地”,然后再实现“贴地飞翔”的?
宫敏捷:我经常从一个读者的视觉去考虑这个问题,我希望我看到的作家及其作品,是在用一个与众不同的角度去表达其作为个体十分独特的对生活的真实看法,如果不是,我几乎很难看下去。一个作家,如果只是在重复他人,或者是把许多人的东西拼凑在一起给我看,那我为什么要看他的东西呢,直接看之前那个(些)人的不就得了。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城市题材在写作难度上,比农村题材大很多,因为城市比农村更复杂,更浩渺,更难处理。农村相对的封闭性及独特的生活习惯及文化沉淀,呈现起来,具有先天优势,而要想把城市生活写出个人独特的感受,确实挺难的,因为全世界生活在城市的人们,似乎都在重复着一样的生活,面对着一样的问题,就业、看病、上学、社保、房子、车子等等。把这些生活写成一个一个的故事并不难,难的是如何让他们“贴地飞翔”。我所说的“贴地飞翔”,指的是文本夯得实,故事接地气,文学上又要有飞扬的神采,用王安忆的话说,要有“奇情”。不管怎么说,文学创作,就是在现实的基础上虚构另一个现实出来,前者贴地,后者飞翔。
以文学的方式返乡
记者:一部《锅圈岩》,你以文学的方式返乡。钟书阁活动现场与你对谈的冉正万老师,则以文学的方式守土。“以文学的方式返乡”和“以文学的方式守土”背后,实质上代表两种文学观和文学路径。能不能请你就此谈谈?
宫敏捷:有贵州的评论家说我是“墙内开花墙外香”,我明白他的意思,说的是我写的素材乃至于题材,之于贵州的作家们并无特别之处,又为什么能引起注意,我想原因就在于我是带着“距离”审视的。这其中的差异又涉及到许多创作意识方面的问题。也有外省的评论家说我“始终保持回望的姿态”,他们所说的,更多是小说本身具体呈现出来的文本效果,又不是针对个人了。我更喜欢大家关注的是我的作品,而非个人。如果不是宣传需要,我其实是个话挺少的人。
记者:假设你当初没有走出贵州,而是留在贵州创作。你能想象你的写作方向么?会是另一个曹永么?
宫敏捷:我求学的过程,从未想过自己要考什么大学,也从未想过自己长大后要从事什么职业,我唯一操心的是,怎么样才能继续保持读书的心态,看越来越多的书;我现在做到了轻职业、重阅读与写作。写作是我阅读之后的自我表达,表达我对世界的看法、生活的看法。如果留在家里的话,我不可能成为另一个曹永,我应该根本就不会写作。我们那儿,没有阅读也没有写作的环境与氛围,真是那样的话,文学对我来说,就是奢侈品了。
记者:你是作家,也写评论。《锅圈岩》之后还出版了一部评论集《写作,找到表达自己的方式》。从某种意义上,“作家”是“评论家”的一次“返乡”实践,因为评论家有一个属于自己理想的“文学家园”,看别人的作品总是挑这挑那,还不如自己动手去构建。对你而言,评论家和作家的身份,哪个在先,哪个在后,哪个是因,哪个是果?
宫敏捷:我其实不想说自己是评论家,不敢当,只是常有朋友约我写书评,我自己看书越来越多后,也想表达一下自己对这些作品的看法,还有就是,总有一些作家朋友会找我时不时聊一聊文学,说得多了,一些自成体系的,能够代表我对文学看法的东西,就在心里沉淀下来,于是我在小说创作之余,把他们写了下来。但是我一直说,写评论,是阅读与小说创作之外的副产品。我自以为成体系的东西,我的小说观,我更想的是用小说去表达,而不是写评论,或者是那些更像是体验的文字。我那些所谓的评论,是用来跟身边的朋友,彼此十分熟悉的朋友聊天的,而小说,我希望被更多的人看到,越多越好,离我越远的,越好。
记者:你出生的乡土与生活的城市,感觉处于“封闭”和“开放”的两端。你和你的家乡、和现在定居的城市,三者之间是怎样的关系,能构建出怎样的体系?
宫敏捷:我来深圳二十多年了,二十多年里,我做过许多工作,收入由低到高,然后结婚生子,安家落户,这个漫长的过程,就是我融入这个城市的过程,而融入这个城市的过程,其实是我不断结交各种朋友的过程。我们常常听到别人说,某某城市是他的第二故乡,那是因为城市的每一个街角,每一条街道,都有他的足印,甚至发生过故事,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回忆;他走到任何地方,都会想起一个能够说得上话的朋友,打一个电话,朋友就会来到身边,陪他喝一杯酒,随心所欲地聊聊。一个人对一个城市的感情到了这个状态,就说明他已经“深陷其中”,不可脱身,也不可能脱身了,简单点说,对于真正的故乡,已经可以不用回去了,因为生活的城市,已经让他没有漂泊感了。这个时候,带着岁月的烟尘,时间的距离,心理的距离,再去打量故乡,而自己又正好有一支笔,可以冷静又客观地书写故乡时,我才能上升到文化上、历史上、人性上去重建它。每一篇小说都是在为它开枝散叶,写得多了,就自成体系了。
(图文宫敏捷提供,本报略有删改)